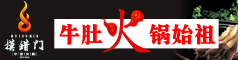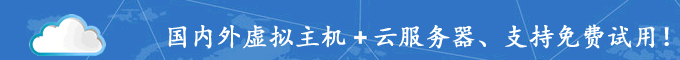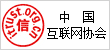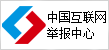|
走进老丹村,斑驳脱落的围墙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等有关禁毒的宣传标语若隐若现。在一处老宅子墙体背后,“某某吸毒死了”几个涂鸦大字依然能看得清。 这一切,似乎都暗示这里曾经受到的“毒害”之深。 丹村,位于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尖峰岭下,是一个有着500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清代中期,丹村出过4名贡生;革命战争年代,丹村有28位烈士为革命捐躯。 然而,这样一个颇具文化和红色基因的村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沉沦:毒品蔓延、抢劫盗窃等治安问题多发,外地司机一度不敢进村,连外地姑娘也不愿嫁进来。丹村一度成为海南西部边陲有名的“吸毒村”“问题村”。用老丹村人的话说,“以前外出说自己是丹村人,都会没面子”。 如今,走进“新”丹村,一块写有“文化兴村”“红色传承”的石碑矗立在村口,一排排独栋小楼映入眼帘,村路纵横交错,村民三五成群在酸梅树下纳凉,袅袅炊烟勾勒出新农村新画卷的勃勃生机。 村两委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写满了村里大家族的族谱、家训,办公桌上还堆放了由村两委编撰的《丹村志》和民间文化刊物《龙沐湾》,19本村民的个人作品集依次排放。连任5届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上强笑着说,丹村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了,现在愿意嫁到丹村的外地姑娘越来越多,丹村人的面子又回来了。 被拉下水的村民 “通过负面教训让村民反思,懂得村衰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辙,从而少走弯路,让丹村长盛不衰,造福子孙后代。” 《丹村志》开篇的这段话,直面了丹村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将毒品带回村里,丹村的噩梦就此开始。 当了30多年村干部的石献奇回忆,那时村里人大部分都在家务农,种水稻、种瓜菜的都有,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即使农作物有收成也难以运出去,大家挣不到什么钱。 村里劳动力大量闲置,部分村民为谋生计,开始远走他乡到外地打工。由于缺少约束,外出务工者中的一些人染上毒瘾,并传给同村青少年。 大多数吸毒者都有相似的经历:最初接触毒品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无底深渊。 今年34岁的阿光(化名),皮肤黝黑,眼珠深凹,鬓角已有几缕斑白,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苍老许多。阿光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有一天,他和几个带着“白粉”的年轻人去了村东头一间废弃的小房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阿光的噩梦从此开始。 持续吸了四五个月后,阿光感觉自己彻底离不开毒品。当年10月,正和朋友一起吸毒的阿光被警察抓住,并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白粉’就是毒品,但不知道毒品具体有什么危害,以为跟抽烟一样。”石献奇说,当时家里有吸毒的孩子,村干部向家长提醒,家长多数时候会不高兴,认为毁坏了孩子的名声,所以一致对外称“孩子没有吸毒,就是在吸烟”。 “失控”的村庄 大约1993年至2002年,丹村“失控”了。 彼时,乐东县中学的化学老师石璜从县城坐班车到佛罗镇后再换乘三轮车时,往往会遭三轮车司机拒载。 原因是丹村村口聚集了一帮社会闲散青年,除丹村人外,这帮青年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陌生人。 那时,在贫困的丹村,青少年因念不起书,辍学在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村子里几乎没有文化娱乐生活,连电视机都很少。漫长而无聊的日子里,部分青年很快就跟“吸粉”的人混到了一起。 现年72岁的石璜回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因为缺钱买毒品,吸毒的人偷家里东西卖钱,没有东西可卖了,就出去偷、去抢,村里的偷盗情况越来越多。 “为防止被偷,一些人家晚上甚至要和猪牛羊家畜一起睡。抽水用的水泵丢失,也是常态。”石璜摇摇头说,作为人民教师的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他曾找一名村干部反映情况,谁料这名村干部的两个儿子也在吸毒。 这名村干部回忆起往事眼含泪花,“作为一名母亲,你能想象到拿着藤条抽打儿子后,一家人抱头痛哭的场景么?我恨贩毒的人!”她咬着牙说,继大儿子吸毒后,有一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她发现小儿子居然也在自己的房间吸毒,她整个人崩溃了,想死的心都有。 如今,她的大儿子戒毒成功,小儿子依旧被关在戒毒所。 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至2002年,是丹村吸毒情况最严重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全村吸毒人员明显增多,到2002年,全村5000人中吸毒的就有70多人。 时任佛罗镇派出所的肖姓干警回忆,那时候,每到过年都是村里最乱的时候。他不得不联络村里所有的村民小组组长,安排专人值夜班,围着村子巡逻,专门抓小偷。 “有时候,半夜村里会打开广播,把村民喊起来查看耕牛是否被偷。很多村民被毒品害得惨不忍睹,整个村子像失控了一样。”回想起那段岁月,他感慨不已。 村支书发起的自我“救赎” 随着村里吸毒的青年越来越多,丹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问题村”。 一些村民纷纷向村委会反映,要求遏制吸毒现象。一些家庭开始主动将吸毒的家人送去戒毒所强制戒毒。 “眼看着家乡沦为乐东县毒品形势最严峻的村庄,辍学青年越来越多,这样的村子是没有未来的。为挽回名誉,必须做点什么。”彼时,在海口做生意的丹村人谢上强有了返乡的愿望。 2004年,在村民的期待中,谢上强当选为丹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这位身高1米8的大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治毒”。 “一夜抓了18个吸毒仔,”谢上强说。他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先张贴宣传标语,制造声势,然后挨家挨户对涉毒青年造册登记,再联系当地派出所采取强制戒毒举措。 谢上强将“治毒”称之为“雷霆行动”。尽管遭到一些“吸毒仔”的威胁,妻子甚至还接到过恐吓短信,但他和村两委班子仍坚持了3年多,并形成了一套奖惩举报机制。 阿光回忆,那次村里动真格了,曾一起吸毒的小伙伴开始四处逃散,自己也被“三进宫”强制送进了戒毒所。 谢上强意识到,救赎才刚刚开始,“除根”还需依靠教育和文化,要从娃娃抓起。经丹村两委班子商讨,他们提出了“教育兴村”“文化兴村”的目标。 2010年,谢上强带领班子成员主动出击,四处寻找从村里走出的乡贤和外出务工的成功人士。谢上强四处打听,辗转多次找到今年73岁的画家王炬光,希望他回到丹村做点事儿。画家被谢上强和村两委班子的真诚打动了。 同样,谢上强还登门拜访了在乐东县城声望极高的退休教师石璜和海口某高校的退休教授王建光。谢上强开始说服在外务工的丹村人,随后,从丹村走出的某企业老总石隆英慷慨解囊,“平时少抽一包烟,节省开支,为家乡的助学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这些从丹村走出的文化人和生意人被这位村支书感动,村里的一些老党员也开始四处游说,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助力。2010年底,丹村成立了教育基金会,成立当天便募集到了50万元。 基金会奖励考取海南中学的初中生以及考取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按不同金额分别予以奖励。此外,基金会还向丹村小学优秀教师和在校优秀学生颁发“奖教金”,由王炬光、王建光、石璜为获奖师生授奖。 作为从村里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今年71岁的王建光在村两委的支持下,联同从丹村走出的文化能人开始编纂《丹村志》,并耗时3年编纂了族谱、家训,启发村民自我管理。 经过多番商讨,丹村制定了包括检举揭发贩毒者和偷盗抢劫在内的18条“村规民约”。 丹村重生 逐渐,村里男女老少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开始从“谁家孩子进去了”变成“谁家孩子读书又获奖了,谁家孩子又考上大学了”。 “从被毒品侵染到现在重拾读书氛围,丹村的变化值得思考。”时任海南旅游公司三亚分公司总经理郭义忠一直关注家乡的变化,这位青年诗人在谢上强的力劝下,也回到了家乡。 2012年7月,郭义忠自筹了3万元出版了第一期丹村民间文化刊物《龙沐湾》,旨在立足丹村,搭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这位长期活跃在天涯论坛乐东板块的青年没有想到,第一期印发后得到了全村乃至佛罗镇老百姓的支持。“一个外地的老板主动打电话,问我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他,当时很感动。” 《龙沐湾》还激活了丹村乃至整个佛罗镇和乐东县城老百姓的创作热情,投稿源源不断。截至目前,《龙沐湾》已出版10期。村两委还鼓励村里的文化人出版个人作品集,目前已有包括民间诗歌、小说、画册、书法在内的19本个人作品集。 文化的力量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们。55岁的村民陈泰武将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成了丹村人的一段佳话。曾吸毒“三进宫”的阿光如今已是一名水果批发商,也是两名孩子的父亲,“现在一心想着赚钱养家,将孩子供到大学”。 曾受过奖励的大学生谢祖梁去年发起成立了“丹村暖乡大学生志愿队”。村两委将办公室腾出来,18名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寒假免费帮扶村民子女补习功课,并集中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解孝敬礼仪、安全常识等。他们还开展“洁净乡村行动”“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系列志愿者爱心活动。 文化的力量慢慢汇聚。从2014年至今,每年春节前,丹村都会举办文化艺术节。期间,海南书法界知名人士都会义务前来为丹村群众写春联;王炬光等画家义务挥毫为村民送年画;摄影师为丹村群众义务拍全家福等。村两委还组织村民开展象棋比赛、书法、剪纸、猜字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 艺术节结束时,由村民自演的“丹村春晚”成了年度压轴大戏。“演员都是咱村民,不看演出不算过年。”年过五旬的村民张文珍自幼爱好文艺,“丹村春晚”给她和姐妹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家乡逐渐摆脱了‘吸毒村’的恶名,我们还要让村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才是丹村真正的重生。”谢上强告诉记者,丹村多旱田坡地,适合种植热带高效经济作物。近年来,丹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夯实水利基础设施,金钱树、哈密瓜、空心菜等许多作物也随之让村民的口袋鼓起来,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元,很多人家都盖起了三层小洋楼。 如今,连任5届的村支书谢上强又带领班子成员四处奔走,希望丹村新建一所小学。谢上强说,这几年村两委还发动村民沿着村路两边种植了3000株凤凰花,明年花开,丹村将是一片花的海洋。说完,他笑着唱起了一首由村民谱写的歌曲《请到丹村来》: 请到我们丹村来, 丹村大地诗如海, 凤凰花儿开不败, 酸梅汁儿美滋滋, 哈密瓜儿甜蜜蜜, 欢迎你到丹村来。 |